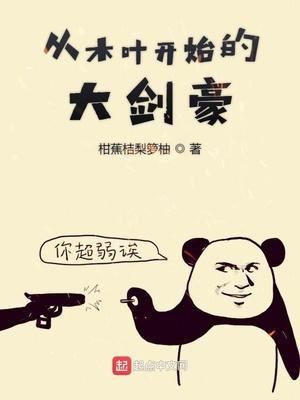精英小说>表姑娘有身孕了 > 第77章 收尾中(第3页)
第77章 收尾中(第3页)
离了宣州城,至泉州时天气就不再冻的人伸不开手,这里也不见落雪,坐上船后,更是一连好几日的晴日。
船只行驶的快,上面只坐了他们几人,容温起初还是将自个闷在船舱里,逐渐也开始走出船舱到外面来晒晒太阳。
待到离得江南越近,不止天气越发的暖,容温心里也有一种莫名的欢喜,是一种身体本能的熟悉,也是这一年时日里的念想。
自幼长大的地方,终是能勾动内心的情绪。
行了有十几日,离的丹水仅剩一日水程时,容温将她带着的最后一壶桂花酒提着来了船板上,见顾慕正在灯下翻阅书卷,她在他一旁的板凳上坐下。
壶中酒倒在杯中,容温递给他:“二表哥尝尝。”顾慕放下手中书卷看着她,眉心微动,拿起杯盏用了口:“桂花酒。”
容温对他点头,随后问他:“我给你留了两壶在木莲院,你可用了?”想来是没有,后来他们一同回了恒远侯府后,她没有再回去过,他好似也一直住在侯府里。
果真,顾慕与她道:“你放哪里了,我怎不知?”容温认真与他说着:“我给你放在书案左侧的木柜里了,”她顿了顿:“其实,我都想带回侯府的,想着既是你我一同酿的酒,也当给你留两壶,不能太贪心。”
这是才酿下的新酒,她住在顾慕的府邸中时与他一同在木桂院摘的桂花,照着酒老翁给的单子酿的酒。
当时,酿的并不多,想着落下的桂花瓣都给收起来了,日后还有的是时间可以酿酒,如今看来,当时应多酿些才是。
顾慕瞧出了她的心思,嗓音平和道:“桂花常有,人亦在,你若喜欢,日后再给你酿。”这会儿是夜间,顾慕眸光落在她被烛火映的澄透却略显苍白的脸颊上,与她说着:“气色不好,不该走水路的。”
容温被他看着,下意识抬手捏了下自己的脸:“有吗?我觉得这回比我去上京城时舒服多了,那会儿整日闷在船舱里,还吐了好几回呢。”
说到这里,容温眼眸微动,将杯盏里的酒饮尽,再添一杯时与顾慕说着:“二表哥知道在宣州城外的那夜,我心里在想什么吗?”
顾慕看着她,一副洗耳恭听的神色,难得她主动与他提起宣州城外的事。
容温手肘撑在膝上,单手托腮抬眸看着顾慕,嗓音浅浅的说着:“那夜,我跪在你面前,当时在想,若眼前这位公子肯救我,带我离开平江王世子,再将他身上暖和的大氅给我裹在身上,我就对他以身相许。”
她说完,目光一寸不错的瞧着顾慕。
顾慕亦是垂眸看着她,眸光深邃,将容温的神色打量了一遍,他如何能看不懂她是何意,这会儿与他说这些。
是故意的。
还记着仇呢。
夜风微凉,好在一旁的铜盆里燃着炭火,船只拨动水面前行,容温这会儿一手抵在膝上托腮,另一只手上举着杯盏。
顾慕看着她,将手中拿着的杯盏上前想要与她对饮,却在将要触到容温的杯盏时,被她坐直身子给躲了开。
又是故意的。
顾慕轻笑,默默将杯中酒饮尽。
容温看了他一眼,与他说着:“二表哥想用一杯酒就与我泯了恩仇,不行。”她说着,也将自个杯盏里的酒给饮了。
顾慕看着漫无尽头的黑夜,嗓音平和与她说着:“日后每年秋日,我都酿桂花酒给你喝,与你赔罪。”
他倒是还想再问上一句,以身相许,可还作数?
容温笑了下,站起身来给他的杯盏添满香甜的桂花酒,随后边走向她的船舱边道:“夜色深了,二表哥回船舱歇着吧。”
她离开后,顾慕站在船板上,颀长身影与夜相融,直至深夜,也未走回船舱。
——
翌日午后,船只在丹水靠了岸,容温早些日子就已写信送至丹水安府,因着在宣州城逗留了数十日,安家老夫人命人整日里在这候着。
容温他们刚下了船,就有一二十出头的男子手中拿着画像走上前来,先是看了眼容温,随后又是看画像,嗓音里含着欣喜:“表妹,你终于是到了。”
来接容温的这人是安家三房次子安煊,本来这事是轮不到他的,奈何他在书院里不成器,被赶回了府上,老夫人对他发了话:“临近年关,府中其他人都有正事,你表妹许是在路上耽搁了,你就日日守在码头候着吧。”
老夫人对他说了狠话,于是,他在码头这里一待就待了近半月,真可谓是风吹日晒,还不如在书院里听之乎者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