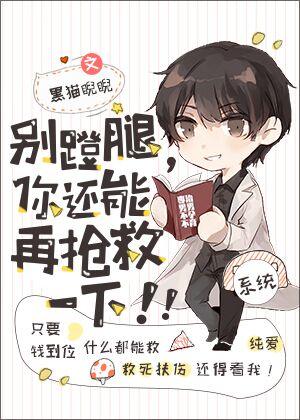精英小说>耗尽春色 > 第148章(第1页)
第148章(第1页)
他嘴唇咬的血红,眼神紧张且担忧地落在自己身上。
陆曜山还穿着病服,圆领衫露出一截脖颈,盛昔陶一眼便看见他后颈上的青紫。
他心脏顿痛一时无法站立,陆曜山一瘸一拐地走到了他面前。
他将手递给他,轻声问:“怎么还没走?”
盛昔陶握住他的手心,想站起来却双腿发麻向后倒去,幸好一只手臂及时将他拦住。
“啪”地一声,拐杖掉在地上,陆曜山却只看向怀里的人——好在是接住了。
盛昔陶听见头顶传来一声无奈的笑声。
陆曜山说:“想投怀送抱就直说,你这样我都不习惯了。”
盛昔陶便立刻站直了身体,他想反驳我可没有,一抬头却哽咽了。
陆曜山的脸色比刚才还要差劲,白得像一张薄薄的纸,他眼底凹陷,嘴唇干裂,头发乱糟糟的,搂着他的时候身上没了肌肉,硬邦邦的骨头显露出来,整个人疲惫不堪,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折磨。
陆曜山见他眼眶红了,不由忙哄:“我错了,你想抱就抱,想怎么抱就怎么抱好不好?”
盛昔陶就用力地抱住了他,谁知怀里的人突然“嘶”了一声,像是被触到伤口,陆曜山浑身一激灵。
盛昔陶回过神,顿时不敢抱他了,双手忙要撤回来。
陆曜山却叫他别动,他把盛昔陶抱在怀里,脸埋在他的脖子上,闷闷地说:“让我抱一会儿。”
可疼死我了。
相见的时光过得比想象中要过得快,一晃到了中午,没等把陆曜山送回病房,半道上,陆骢和白筱落便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盛昔陶和姜河只好先离开了医院。
陆曜山和他们约定了每半个月见面,分别时又依依不舍地亲了亲盛昔陶,看着他通红的眼睛说:“下次来不许哭了,我会心疼的。”
盛昔陶勉强点了点头,他的视线落到陆曜山的后颈,见他下意识扯起领子掩盖,心里饶是难过。
离开医院后,一切似乎并没有好起来,得知真相或许有时会加重不幸。
盛昔陶一连做了好几天的噩梦,他午夜惊醒,看到陆曜山被绑在房间的椅子上浑身发抖,大声疾呼,可是等他慌忙下了床想要解救他,却发现椅子上冰凉一片。
紧接着,一回头又发现陆曜山躺在地上,他的四肢百骸碎成一片,盛昔陶跪下去想捡起来拼到一起,可是怎么拼都拼不对,瞬间,那堆碎片又化成了一滩血水,血水中浸泡着一颗深红色的器官,盛昔陶把它抱在怀里,霎时,那器官又发出凄厉的尖叫!
“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姜河被隔壁的惨叫惊醒,急急忙忙地跑进来,只见盛昔陶坐在床上脸色惨白地大叫着。
他上前安抚他。
“盛先生,盛先生!”
“你做噩梦了,没事了。”
盛昔陶浑身湿淋淋的,汗水浸透了衣衫,惊恐布满他的双眼,他抓着自己的头发,被呼叫声着拉回现实。
可在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安静了几秒后,又“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呆在公寓里的每一天,几乎都在房间对着四面空空的墙壁和空荡荡的床榻。
盛昔陶觉得这一切都没意思极了,不对劲极了,他抓耳挠腮,极尽努力地想做些什么改变,可现实像一道深井将他堵死在了阴暗中,他只能抬头望着遥不可及的巴掌大的天空,看着自己日复一日地被禁锢。
就在他几乎绝望之际,事情的转折赫然出现。
周五晚上,盛昔陶洗了个澡,因为明天他要去医院探望陆曜山。
似乎只有这个时候,他的精神才会好那么一点儿。
站在镜子前,他看着自己消瘦的肩膀,凹陷的脸颊,和乌黑的眼圈,他想起陆曜山说下次见面不要哭丧着脸,于是对着镜子尽力想扯出一个微笑,可惜似乎是徒劳。
就在他要脱下衣服走进淋浴间时,门口突然响起一阵脚步声,紧接着,姜河急切地敲响了他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