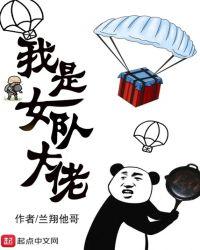精英小说>反派被迫营业 > 第366章(第1页)
第366章(第1页)
崔嵬退后一步,洞内幽静无声,只有无穷无尽的苦寒,他并没有再继续看下去,已明白结局。
火血永远不会停歇,血沸人冷,若未东明寻常身死,皮囊一腐坏,火血定然沸腾而出,蔓延千里,他天生就是封存火血的容器,如今又中尸毒,人虽死犹生,身受冰火煎熬之苦,神思昏昏,无知无识,永生永世沉眠此地。
直到火血消融,霜花不再。
白鹤生的修为不足,不敢踏入此地,只能在外头等待,他听见崔嵬走出来的动静,不动声色地询问道:“我们到处都走过了,并没有另一位前辈的身影,若他不是遭遇不测,恐怕现在正在神域中。此地蜃毒浓重,不可久留,我们还是先离开为上。”
崔嵬知他说得有理,点头答应后,二人按照原路离开了山谷,来到外面溪流之中。
入内时月华盈满,等二人来到外头,已是天光大亮,虽才过去几个时辰,但对崔嵬而言恍若隔世,不过是短短几个时辰,于观真下落不明,未东明身陨苗疆,他心中沉重不已,却已下好决断,便先转过身来道:“多谢阁下出手相助。”
“哼,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我不会谢你,你也不必谢我。”白鹤生嗤笑一声,随后又垂着脸想了想,又道,“你要是现在没有主意,我倒是有个想法。”
崔嵬沉吟片刻:“不知阁下有何高见?”
“高见算不上。”白鹤生道,“馊主意我倒是有一个,不知道你听不听。”
崔嵬垂眸道:“请说。”
“琼玉身上虽有神血,但到底修为浅薄,要是找她帮忙,伤命事小,失败事大。”白鹤生有心想撇开厌琼玉,他知晓若让小师妹卷入这摊浑水,只怕她不死也要脱层皮,只是在缥缈峰上向来只谈成败不谈情义,因而言语中冷冰冰没半分人情味,“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到那位于前辈,此事该找大巫祝。”
崔嵬听得不由皱眉,到底没有说出什么,而是专注在这件事上,他知晓大巫祝是何等麻烦的人物,纵然做了同样的打算,仍不由得叹息道:“恐怕大巫祝不会答应帮忙救人。”
“权衡利害,他会答应的。”
在于观真与未东明离开之后,白鹤生就很快察觉到了不对劲,他向来浅眠,又甚为警觉,很快就察觉到二人的失踪。这些时日下来,白鹤生隐隐约约意识到他们二人似乎在找什么东西,加上晚间不断提及的起死回生之术,他大概猜出厌琼玉为何坚持来此,有何所图。
因此白鹤生才会半夜来访“赤霞女”,只是没想到见到的不是女娇娥,而是藏锋客。
而进入幽谷之后,未东明又带来了更令人震撼的消息。
尘艳郎就在此处。
崔嵬叹了口气,并没有说话,大抵是在考虑这件事的可行性。
其实白鹤生如今已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些许人的身影,只是谁也不曾告诉,若非如此,也不敢孤身一人出行,他看见眼前对自己毫无防备的模糊人影,不觉捏了一把汗,轻视残缺之人几乎是人的天性,未必是轻蔑,而是一种心态。
对瞎眼之人不必遮遮掩掩,对耳聋之人不必注意谈话声调,而哑口之人当然也不必忧心他们会泄露秘密。
白鹤生知晓这很有可能是自己唯一能胜过崔嵬的机会,却又不免迟疑起来,他向来对所谓的道义公平不屑一顾,自无这方面的忧虑,可是如今的局势紧张,他也当权衡利弊。
尘艳郎狡诈狠辣,此刻若偷袭崔嵬,且不论败,纵然是赢,也谈不上划算,到头来仍是因小失大。
如此一想,白鹤生的杀意顿歇,只是伸手轻轻握住峥嵘,却觉峥嵘剑身颤抖不止,竟已出鞘半截。
他心中顿觉不好,知峥嵘定是方才感到杀意,此刻已是躁动无比,立刻伸手去压制剑柄欲归剑入鞘,哪知峥嵘气盛,不退分毫。
峥嵘乃不世之器,若非白鹤生这一双剑骨,恐也难压制它。
正当白鹤生想要千方百计地压下峥嵘的杀意时,忽觉得腕上一沉,虚虚搭上来几根手指,柔软、冰凉,还留存半点美人手的香气,崔嵬不知道何时已近在眼前,不由得心下凛然,只觉得那手指慢慢顺着腕子一推,峥嵘如水的剑身便无声无息地滑入剑鞘,头一遭显出温顺来。
“道长路险。”崔嵬并没有拿走峥嵘,而是很快就将手收了回去,云淡风轻道,“赶紧动身吧。”
尽管崔嵬什么都没有说,可白鹤生已经明白,倘若方才出剑,死的人绝不会是崔嵬,这个男人已将十年前的他远远抛在身后,然而那昔日之影,至今仍是白鹤生的梦魇与目标,他终于明白自己跟崔嵬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手上劲力顿时一松,软绵绵地搭在峥嵘之上,遍体生寒。
白鹤生的心在跳,他倏然想起了自己当日握住于观真的手,已忘了那是什么滋味,只听见了如鼓的心跳声,无意燎到他,又烫又冷。
他没学过,没尝过,对这种情感一无所知,只知晓峥嵘是天下至宝,只看得见有形之物,不知珍爱的若非凡夫,就是愚昧之人。
愚昧的凡夫正在前面走,对峥嵘视若无睹,全无半分留恋,是这剑依恋他,分离数年仍心甘情愿地臣服。
崔嵬超然脱俗,目下无尘,他的心不曾为外物所动,却为一人而动。
白鹤生忍不住道:“你一点都不怀疑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