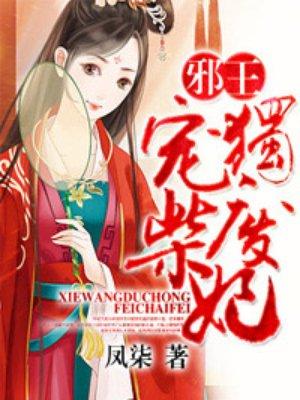精英小说>反派被迫营业 > 第316章(第1页)
第316章(第1页)
崔嵬重新调整了下睡姿,将两只手搭在被子上,他们只睡一床被褥,两个人不得不再度紧紧贴在一块,他闭上了眼睛,像是真的只想要一场同床共枕:“我想留下来,一定是要想说些什么吗?”
于观真下意识否认:“那倒不是。”
接下来崔嵬就没有再说话了,他的呼吸匀长,似乎说睡就睡了,这让偶尔饱受失眠困扰的于观真非常羡慕,只好在被子底下悄悄地伸出手去摸崔嵬的手,对方并没有抗拒地被他捏住几根指头,上面的茧子薄了很多,摸起来犹如羊脂白玉。
他其实有许多话想说,却不想跟崔嵬说,而除了崔嵬之外的人,他又懒得张嘴说。
于观真微微侧过头,靠在了崔嵬的肩膀上,不知道为何,心底忽然生出一种极强烈的渴望,想要哀求、挽留崔嵬留在自己的身边,不要去什么天玄门,他们一道去苗疆,在结局到来之前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刻。
又或者于观真抛下一切,跟着崔嵬一道去天玄门,去应付那个笑呵呵的长宁子,去翻遍尘艳郎的每道痕迹,去追寻起死回生之术最后的真相。
他想将这些贪婪的念头尽数告诉崔嵬,也知道崔嵬会很耐心地听,然而听完之后,他们仍会各自启程,去往自己的方向。
所以什么都不必说。
崔嵬总是比他看得更快更远,他们所相伴的时间太少,实在没必要浪费在那些一遍遍确定过的事情上。
而另一个让于观真感觉到不安的念头又再层层翻涌上来,他曾怀疑自己死去,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以为尘艳郎约好了要来救未东明,发生了意外才没办法解决;而如今看来,似乎又是尘艳郎早已预料好的密谋安排。
于观真的心头翻涌过许许多多的念头,最终不堪重负,还是将沉重的眼皮合拢,慢慢睡去了。
两人一夜都无梦,于观真也没有给崔嵬服侍自己的机会,甚至于他睡醒时,崔嵬才刚醒不久,正坐在床边系那根浅蓝色的腰带,将他的腰身勒出来。
于观真趴在后头看着他,觉得很惬意,很美好,巴不得往后每个日出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只是人不会看厌,腰带难免会看厌,可以多挑几根,换着来系,苗瑶的五彩带其实想想倒也挺好看的。
他仍记得崔嵬穿瑶族衣服的模样,很飒爽利落。
崔嵬好像后面长了眼睛一样,将头发从衣物里抽出,半垂着脸问道:“起来吗?”
“起。”于观真闷在被子里模模糊糊的发出声音来,他舒展开纤长的四肢,像是朵清晨才绽放的花,懒洋洋的,眉跟眼都沾着晨雾,格外黑亮,“你都喊了,我怎么能不起来。”
崔嵬大概是笑了一声,也可能没有,反正等于观真下床的时候,他脸上已经没有什么表情了,还帮着递了衣服,于观真坦坦荡荡地站在地上,张开双手道:“不是要服侍我吗?”
“好。”崔嵬有点无可奈何地看着他,然后将衣服一件件套在他身上,不敢怎么用力,可有时候还是像要于观真的胳膊拧下来,于观真就哎呦呦地叫起来,好像骨头要断了一样,崔嵬实在没办法了,就问道,“真的这么痛?”
于观真厚着脸皮说:“那倒不是,不过我不叫,你怎么有理由心疼我呢。”
崔嵬就往腰带上狠狠束了一下,这下于观真是真的要断气了,一下子弹起来,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藏锋客好整以暇地摸了把毛,手指在下巴上滑过,好似真的在抚摸一只猫,他慢条斯理道:“来,抬脚。”
边说着就要蹲下去。
“这个我自己来。”于观真松了松腰带,跳着脚离开了崔嵬的手臂范围,他赤着脚,脚面光滑雪白得如同一颗刚剥开壳儿的鸡蛋,青色的血管显得格外明显,他跳了两步,让人想起滚落在地的珠玉,也会发出这样有点沉闷的声响。
崔嵬摇摇头,捏住了于观真的脚踝放在自己膝头,将袜子与鞋一点点套上去,然后说道:“清晨起来还有点寒气。”
这口气活像他是什么会感染风寒的普通人一样。
昨天被他捏在掌心里的几根手指忽然变得既不软,又不柔,反倒钢铁似的钳着他的小腿肚,等着将他完整包裹起来。
于观真一下子不说话了,只是提着脚,保持着金鸡独立的模样任由崔嵬作为,血色慢慢涌上脸颊,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等到崔嵬在自己腿上拍了拍,他才后知后觉地换了只脚。
等到漱口吃饭的时候,于观真都没有再说什么别的话。
崔嵬在于观真的房间里喝完了他们在白下城的最后一碗粥,两个被剥得光溜溜的水煮白蛋盛在碟子还没彻底凉透,剥他们的人已经走得很远了。
他们没告别。
于观真望着天,慢慢把那两个蛋拆开,他不爱吃蛋黄,觉得像是吃满嘴的土,又腻又生粉,然而等咽下最后一口粥时,他还是将两个蛋黄分作四口吃了,蛋黄将唾液吸干,粘做一团滚下喉咙。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跟于观真以往吃过的每个蛋黄都一样,可不知为什么,于观真就是特别乐意吃这两个。
等到稍晚些,莫离愁才知道他们要前往苗疆,看起来有点心神不宁的,直到快启程时才提出了辞行。
未东明很是惊讶,他们三人自离开剑阁后向来是形影不离,便饶有兴趣地问他:“那你要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