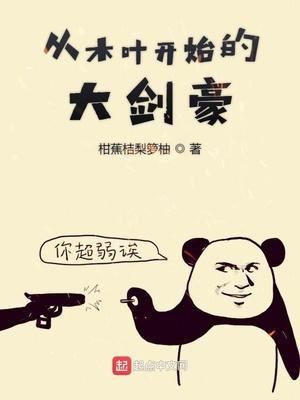精英小说>爱人花碑 > 第16章(第1页)
第16章(第1页)
末日复兴派的演出切到下一个节目,浮士循着周围人的欢呼瞥向那个简陋的舞台。
中央摆着一个黑色的生锈长椅,上面坐着一个衣衫破旧的男人,他的衣装是末日复兴派的特色。
发声的东西只是手风琴、男人的口哨以及沙哑的嗓音。
这三者的音色本应该很安静,但屋子里每个角落却都能清晰地听到,它像一场雨。
浮士听不懂他的语言,所以在他的耳中,歌者吐出的字节前后缠绵在一起,句子像诗一样得长。
“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无底洞’。是不是很奇怪?”阿仅也望着台上,似乎经常来这里似的,她和浮士讲述道,“这里的常客说,他年轻的时候是太空站的流浪汉,搭乘运输飞船来到行星岛屿,爱上了褴褛之人的一个调酒姑娘。就这样,他一直留在这里唱歌了。至于为什么取这样一个怪名字……是因为他在恋人死去的后几年,开始沉迷于投资地下生物实验室的仿生人技术。可他自己明明都是身无分文的。”
社会结构成熟起来的太空站仍旧出现了贫富差距,和地球没什么两样。认为科技进步就能消除人类社会一切根深蒂固的顽疾,其实是一种傲慢。伦理给生物科技上的锁仍然没有解开。仿生人研究所被摘去了合法的权力,疯狂的学者们将其转移到了地下。他们能残喘至今,全靠一些同样痴心妄想的富豪、普通人、流浪汉的投资支持。
“这些投资者的目的不同,善恶混杂。但其中有很大部分人,是想通过所谓科学的途径再见一眼爱人、亲人、朋友们生动鲜活的面容。即使他们知道,仿生人就算有思想也并不是原来的人。”阿仅用下巴指了指台上的男人,给自己的杯子倒上了酒,说,“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给自己取名为‘无底洞’,算是一种自嘲吧。”
她朝台上遥遥举杯,像是协助末日复兴派完成一种行为艺术,笑道:“敬无可救药的偏执。”
观众一阵欢呼,男人也为她单独吹了一段不突兀于主旋律的口哨。
浮士仿佛在歌声里失去了语言能力。
默然良久,他突然问:“你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
“无底洞唱的吗?”阿仅紧接着吐出一串俄语,“名字叫ПoдockoвhыeВeчepa,你也感兴……”
她回头看向浮士,声音戛然而止,眼睛慢慢睁圆,惊讶地道:“……你怎么了。”
浮士先是疑惑地“啊”了一声。继而他发现阿仅的面容模糊了起来,于是伸手擦了一下自己的脸颊,也是一怔。
他原来在不由自主间泪流满面。这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浮士根本没有注意到。
浮士发现,自己的情绪感触竟然已经被年岁磨钝到远远地落在了生理性反应的后面,在手指触碰到泪水的那一刻,他的胸膛才开始泛上一丝酸意。
但这情绪也只是像潮汐一样,漂洋过海地来,吞没一下礁石,又匆匆地退潮了。
“我没事。”浮士将酒喝完,和阿仅告了别,穿好行装,说道,“很高兴和你聊天。我该回去做sts了。”
歌声的尾音消失在身后。
浮士并没有去做sts。
他躲进了飞船的航行舱里,发了一会儿呆,最终决定给陈哀从前的号码拨一次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