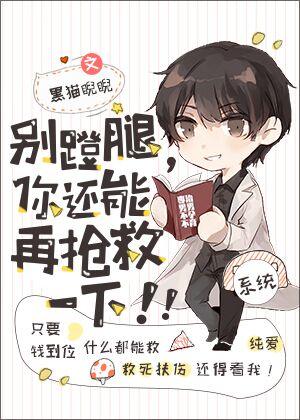精英小说>垂怜 > 第93章 第093章(第1页)
第93章 第093章(第1页)
◎快走◎
翌日一早,礼乐坊门前便围满了人,放眼望去人头攒动,如洒了一地的芝麻籽。
上一回乞巧节,礼乐坊的曲目本是要迭奏的,其中单言白便有三曲,只是当晚翰林院编撰被刺杀,直接封了街,众人并未看尽兴。
加上九公主大婚,这回人便尤其的多,为了给沈非衣庆婚,整个礼乐坊有名的乐师几乎都出动了。
黎民皆站在门口两侧张望,只听那大开的坊门幽幽传出几声琵琶,便有人躁动:“出来了出来了!”
那在门周守着的将士立刻将人流向街道两侧赶,清出一片足能容纳五人并排走的道来。
在众人期盼的视线下,便是清一色嫩绿映入眼帘,个个云鬓细腰,袅袅婷婷走了出来,手里抱着琵琶,在前头引路。
这些只是普通的艺妓,通常都是为乐师做伴。
大约出来六七个姑娘后,这才跟着四位带着面纱的姑娘,这几个乐师穿着浅粉色的襦裙,手里抱着的乐器也都各色不一,随着那乐声步步生莲,仿佛下一刻便要衣袂飘飘回到天上去。
礼乐坊的乐师,越是有名,便越不以面示人,除了这四位乐师外,戴面纱的便只剩下了言白。
翘首以盼之下,终于瞧见了那极高的红木门梁下,走出来一抹白。
那人手里抱着一把不知是何质地的琴,通身玉白,尤其是那身后漆红的门扉,衬得那白便如日光一样刺眼。
言白并未冠发,只用一根白色的玉簪挽髻,垂下的两条白绸混在了发间。
他依旧以纱布遮面,只是他这纱布不同于面纱那般裸透,似乎是更厚一些的料子,带上去后,压根看不出眼下的轮廓。
男人身形颀长,虽清瘦却不孱弱,他并未看着前方,而是半垂着眸,那视线范围好像是只能看到足下及三步远的距离。
前头的乐师早已将他甩了五步之外远了,言白却是抱着琴不紧不慢的跟着队伍。
那些乐师不过走了一段路,便在一辆步辇两侧停了下来,那步辇比普通的步辇要大个两倍之多,上头是鸠羽色的华盖,细长的垂穗做虚掩。
步辇前后左右各有两个抬者恭立。
见言白止步,便有人上前撩起垂穗,侍着言白上了步辇。
待其落座,将那古琴放好,八个人才稳稳的抬起步辇。
男人撩起袖摆,五指按在琴弦上,如玉珠滚落盘中,撩起一阵极为悦耳的琴声。
垂穗左右轻微晃荡,将他的身形裁成细密的无数道,风吹过,撩起了言白的长发,也将那鸠羽色的垂穗卷起。
一片雪花从垂穗的缝隙中斜飞,最后落在了言白的手背上,即刻融化成了透明的水色。
下雪了。
从一开始的稀疏,慢慢的变得稠密了许多,落在枯枝上、灯笼上、红菱上,以及斜飞落在了言白的发上。
那浩大的仪仗一路慢慢悠悠的朝着宫门方向走,那雪便越下越大,路上也极快的铺了一层薄薄的霜。
宫门外有人守着,见是礼乐坊的乐师来了,如今时候尚早,便将其安置在了宫中的司乐坊中暂歇。
紧接着,还不过一柱香的时间,那被太后钦点的准驸马,便身佩红菱挽花,骑马入了宫。
而咸寿宫这边却丝毫没有动静,外头守着侍卫,半点风都透不进来,沈非衣甚至都不知道沈君晔如今正为她办婚来逼沈裴现身。
沈非衣被困在咸寿宫憋得慌,秦玉凝便每天带着她做一些最基础的习武招式活动。
这会儿两人正在院中慢悠悠的练习着招式,一片雪花落在了沈非衣的鼻尖,极快的融化。
沈非衣一方触及还以为是下了雨,便抬眸望向穹顶,才瞧见了细碎的雪花正在往下落。
她当即便收了势,脸上极快的闪过一丝惊愕,再看向秦玉凝时面色却已恢复如常,几乎是同时,秦玉凝也将手收了回来。
甚至连沈非衣都还来不及开口,她便直接上前拉住了沈非衣的手,“表姐,外头下雪了,我们先进屋吧。”
那双手有些冰凉,握着沈非衣的手腕时,有些细微的轻颤,沈非衣反握住她,刚想回应,却见咸寿宫的门突然开了。
外头先是进来三四个侍卫,后面才跟进来八个宫娥,为首的宫娥是在齐妃跟前伺候的婢女。
那婢女在沈非衣跟前停下,微微一福礼,压根不等沈非衣说话便直接起了身,淡淡道:“九公主,请吧。”
说罢,身后跟着的几个宫娥便上前来,强硬抓着沈非衣的手臂。
什么都没说,突然上来就要将沈非衣架走,沈非衣那里愿意,直接抬手甩开,“你这是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