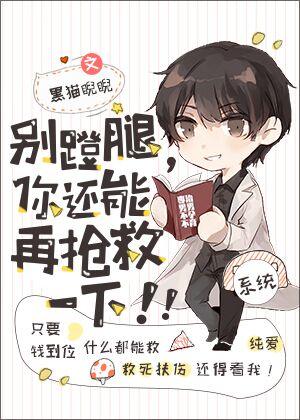精英小说>泊秦淮(原名银瓶春) > 满床笏一(第1页)
满床笏一(第1页)
宝船一走小半月,过了徐州就进了北方。
还在江南时,船回回在岸边停靠,当地官员有耳报神禀报,一早设下酒筵席,着锦绣蟒衣前来拜谒,裴容廷从来不见,只推说身子不爽,托付张将军代劳。然而这回到了山东临清州的码头,他却意外地应了送来的拜帖。虽说是赴席去的,但回来时他神情凝重。
银瓶在卧房里服侍裴容廷脱了大衣裳,出门正遇上静安。
静安忙上前打了个千儿,从怀里掏出两个油纸包,笑嘻嘻道:“姑娘叫我捎的零嘴儿,我都买来了。红油纸里是瓜子儿,黄油纸里是炒栗子。”
“嗳,多谢。”银瓶笑着应了一声,却悄悄招了招手,把静安引到了自己房里。
房里,桂娘正坐在榻上看鞋样子呢,见银瓶带了静安进来,才“咦”了一声,却见银瓶掩上门,从床头小匣子里抓了一把钱给他,低声道:“我问你,大人今儿怎么兴致不大好的样子,可是席没吃痛快?发生什么事儿了?”
静安忙不迭谢过了,脸上还笑着,却叹了一口气,道:“嗳,姑娘还说呢。姑娘在南边儿,不知道,如今这北方的世道可不太平啊!这两年也不知撞了什么邪,春天旱,夏天涝,皇爷又一心开疆扩土,从来不经手这些赈灾的俗事,一应都交给内阁老爷们料理。前儿济南府还下了场雹子,今儿爷下船一看,那起子官爷一味粉饰太平,路上砸坏的庄稼地竟都用布盖上,这个冬天还不知怎么开交呢,如何让爷不忧心。”
银瓶与桂娘面面相觑,桂娘道:“怪道我一进了济南府就觉得凉飕飕的。三年前,我在北边儿时,九月里可没这么冷。”
静安在一旁附和,感叹了一回,就要退出去,却又被银瓶叫住了。
银瓶说:“既然你来了,吃杯茶再走吧。”
于是银瓶净手执壶,给静安点了一碗茶,打开新买的油纸包请他吃东西,唬得静安没口子叫“姐姐”,又连声道:“这可不敢!”
银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你不要客气,你我还不都是大人身边侍奉的人。我找你来,原也不是为别的,只是眼看就要到北京了,大人家里的情形我还两眼一抹黑,怕到了那儿闹笑话,所以想请你提前指点指点。不拘什么,你好歹讲给我听听。”
静安明白了她是要打探裴家的底细,于是存心逞他是裴容廷随身的人,一壁剥栗子,一壁笑道:“既然是姐姐问了,我自然知无不言。只是我来府上也不上三年,只知道近些时候的事儿。那年咱们爷在四川打了胜仗回来,加官进禄的,又赶上裴老太爷殁了,家里人不够使,所以新买了好些人,我就在里头。”
银瓶听了,对桂娘笑道:“怪道大人一直没娶妻,原来是老太爷没了,要守三年孝的缘故。”
桂娘嗑着瓜子不说话,静安又细细说了家里的人口:“老太爷虽没了,但老太太倒还硬朗,家中兄弟三个,咱们爷行二,却不是老太爷亲生的,而是当年抱养来的族中的孤儿。除了咱们老爷,另外两房倒都娶了妻了,大奶奶是宋府丞的女儿,三奶奶是赵千户的女儿。”
桂娘常年和做官的应酬,对官职极熟悉,听这府丞千户都不过四五品,似与裴容廷中书省的身份不配,因此问道:“那大老爷三老爷现在都居着官吗?”
静安笑道:“大爷身子弱,就在家里将养;三爷虽没中过举人进士,现在却做着顺天府的同知,也是皇爷看在咱们爷面子上封赏的。”他想了想,又笑嘻嘻道,“只是咱们府上第三辈儿上人丁不旺,二爷一直没成亲,不必说了;大房这些年都没见有孩子,三奶奶前年养了个女儿,也再没别的动静,愁得我们老太太整日睡不着觉。姐姐如今跟了二爷,赶明儿生了儿子,可就真是裴家的大功臣了。”
银瓶认真听着,脸一红,啐道:“小猴儿崽子,再没句正经话,只会满嘴胡吣!”说着,她站起身把栗子瓜子包了包,一壁往他怀里塞,一壁赶他出去,打开门骂道,“看我回头不告诉老爷,让他打你!”
静安笑嘻嘻的,不想才一出门,正和裴容廷撞了个满怀儿。众人都吓了一跳,静安更是吓得折腿跪在地上,栗子撒了一地,他却只顾求道:“小的不长眼,冲撞了老爷,实不是故意的,老爷饶了小的吧!”
裴容廷掸了掸身上的青丝绢道袍,脸上没甚表情,也不理这茬儿,只问:“方才你又做了什么孽,惹恼了银姑娘?”
生儿子那句虽是玩笑话,可静安万万不敢在裴容廷跟前造次,因此低着头不敢出声。银瓶只怕裴容廷真要怪罪,也不肯说话,反倒是桂娘知道男人爱听什么,故意笑道:“静安打趣银姑娘,说她回头定要给老爷添个儿子,银姑娘臊了。”
静安战战兢兢磕头,道:“老爷,老爷,小的无心说句玩笑话——”
银瓶抿着嘴,偷偷笑了笑,也劝道:“大人饶了他这一遭吧!”
裴容廷没接口,却解下了身上的一只青钦荷包丢给静安,闲闲道:“这是我赏给你的,还不快下去。”
静安愣了愣,忙不迭满口道谢。银瓶皱了眉,急忙道:“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裴容廷低头整理自己的挽袖,瞟了她一眼,似笑非笑道:“他说了一句吉利话,正合我的心意,我自然是要赏他。”
静安扑哧一声笑了,磕个头一溜烟跑开了,倒是银瓶搬起石头自压脚,白讨了个臊。她嗔了裴容廷一眼,便转回身,却见身后空无一人,原来桂娘早已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等过了天津卫,到通州渡口,已经是十月初的事了。
下船的那天,银瓶特意起了个大早儿梳洗,因为是进裴家,不比跟在大人身边可以随意花枝招展,她只好拣那喜庆又不喧宾夺主的衣裳,贴身白绫袄儿,底下银红平金缎裙,罩月白的织罗褙子,掐一圈银挑纱线,扣着蜂赶菊金钮子。淡淡傅粉,松松绾髻,也不甚插戴,只簪金累丝梳钗儿,翠梅花钿儿,耳边坠着米粒大小的珍珠坠子。
她临窗照镜,镜子里是高远淡白的秋天。碧空下河对岸的一脉梧桐,叶子都黄了,被江风吹着,沙沙作响。
这北京的秋天也像是金黄的梧桐树,明晃晃的,枯干,又仓促。
银瓶莫名生出一阵熟悉感,也许就像桂娘告诉她的,她曾经也是北方人。
银瓶下船的时候,裴容廷与张将军早已乘着大轿往正阳门去了。
听说皇爷已亲率文武百官迎到正阳门外,还要奏告太庙宗祠,行献俘礼,设至饮宴,许多流程。执事陈设一连摆了七八里地,鸣锣鼓乐的声响走得老远也一样震耳欲聋。那威震百里,气压秦川的军乐讲的是忠孝节义的故事,威烈中可以闻到沙场上的血腥气,在听惯了水乡南调的银瓶听来,很唬人的。
她乘的则是一顶软帘小轿,顶着满街落叶金色的雨,悄无声息地被抬进了裴府的西角门。
通房也不过是丫头,添一个少一个原本激不起任何风浪,然而裴容廷在这家里的地位举足轻重,况且他又冷清了这些年,房里连个红袖添香的都没有,如今忽然带回来一个苏州的红粉知己,实在是大新闻。
银瓶的轿子才进门,那消息却早已传遍前厅后院,连看角门的老妈子都忍不住往轿帘里偷偷窥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