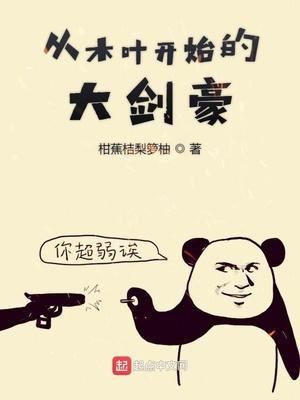精英小说>白栀子 > 开学(第2页)
开学(第2页)
周围都是同班同学,阮白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其实不太会和人聊天,虽然很会说话,如果愿意,也会很讨人喜欢,但那些“乖”、“哄人”、“撒娇”都是限量供应,份额稀少,一般人很难看到。平时不太理人,与大多数同学关系疏离,且没有社交意愿。
因为身体原因,阮白小时候在学校上课的时间不多,很多时候都在家里养病,和同学不太接触,当然也谈不上交朋友,他的性格问题也因此暴露得很晚。直到上高中,阮白一个学期都没有交到一个朋友,他妈妈才意识到这个在家能哄的所有女佣把自己当作亲生小孩疼爱的孩子在外有多冷淡。
也不是害羞,或是嘴拙,他拥有辨别谁好谁坏的能力,就是不愿意去做。
妈妈说阮白真的有点任性,又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不喜欢的事就不要做,过得开心是她对阮白唯一的期望,她会保护好自己的宝贝。
所以阮白理所应当的长成现在的模样,他理所当然的任性。
本该九点钟开始的开学典礼,因为庞大的学生数量,需要参与的老师领导太多,被迫推迟到一个小时后。操场上更加热闹了,几乎都是几人几人凑在一块,彼此介绍,或是说一些别的事。
九月初的太阳还是很晒,阮白闲的无聊,也没有参与讨论的欲望,他用外套蒙住头,塞着耳机听歌,声音开到很大,与世隔绝。
可能是前面太挤,几个人聊天不太方便,聚成一团后,会不自觉往后挪动。阮白感觉到几个人到了离自己不远的地方。
歌曲切换的间隙,下一首歌的前奏还未响起,他听到有人说:“……和严雪临有什么关系?”
前奏进到一半时,阮白还是将音量降到了最低。
一个女声说:“新建的那栋图书馆吗?纪念碑上写的是阮家捐的,但实际阮家是严先生的。”
另一个人问:“严雪临是谁?”
那个女生说:“你是外地来的吧,可能不知道,呆久了就知道他了。”
第一个人问:“还是没说他为什么捐图书馆。”
女生“哎呀”了一句:“不太清楚。他大学也不是在这念的,可能就是愿意支持教育事业呢。我听家里说,不仅是图书馆,艺术院的旧湖周围的园子,也是他捐的,还有一个助学奖金。”
有人感叹:“有钱可真好。”
阮白听了一耳朵,又觉得没什么继续听下去的必要,缓慢调高音量,一不留神,却听到最开始那人说:“那他装什么装?”
音量不小心按到最高,阮白的耳朵突然被炸,吓了一跳,动作大了些,不小心掀掉头上罩着的外套。
那几个人身前忽然多了件衣服,不自觉地抬头,看到坐在不远处的阮白。
这个人真的很漂亮。
在场的其他几人看他第一眼时,所有人的想法差不多都是这样。
比起所有隐藏的内在美好品质,人对某个人、某样事物的第一印象永远来自于外表。
他有一双很好看的眉眼,眼睛略圆了些,瞳仁的颜色很深,看起来除了秀美,还有几分很容易让人心软的天真无辜。
阮白没有理会别人的目光,伸手将掉落的衣服捡起来。
方才那个说话的女孩子“呀”了一声,凑了过来,她的眼睛亮晶晶的,看着阮白问:“你也是我们班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
说真心话,阮白其实没有和在场的任何一人交朋友的打算,但他也不至于格格不入到这种程度,既然没办法继续装死,只好自我介绍道:“我是金融一班的,阮白。”
女孩子也高高兴兴道:“我是柳溪。”
然后,说“那他装什么装”的人开口,他的个头应该很高,坐在那都显得块头很大,穿着无袖衫,耳朵上有好几个耳钉,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张脸也算得上英俊了。他看着阮白,笑了一下,很有礼貌似的:“你好,我叫傅廷。”
他的目光让阮白感觉到不舒服,但阮白没有避开,只是冷淡地瞥了那个叫傅廷的一眼,没理会他。
幸好,接下来也没有留给他们继续交流的时间,主席台上的领导终于到齐,大喇叭喊着让全体安静,巡查纪律的老师在队伍后面走来走去,新生们自觉不再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