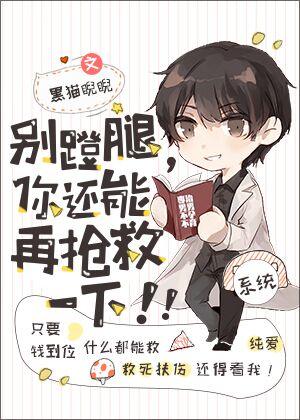精英小说>深情男配身残志坚[快穿] > 琼浆玉液(第3页)
琼浆玉液(第3页)
钟情仍旧倚在沙发靠背上,似乎只是不经意想到这个话题。
“卡佩夫人带过来一个她丈夫新研发出的仪器,能将两个人的感知暂时共享。虽说仪器还不稳定,感应的时间只有数秒,但已经足够了。”
“我共享了卡佩夫人的感知,她已经怀孕六个月。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作为孕育的主体,体会到的情绪与旁观的客体完全不一样。”
所有Omega都极具母性,这是写在他们基因里的程序。仪器启动的那一瞬间,钟情便感受到泛滥的爱意,就算反胃、晕眩也不能掩盖的爱意。
那是卡佩夫人的情绪,浓烈到让作为旁观者的钟情都在某一瞬间,生出为那个尚未成形的胚胎去死的念头。
“世上再也没有哪种关系比母亲和胚胎更亲密无间。母亲占据胚胎的全部,谁来也抢不走,而胚胎接受母亲全部的喜怒哀乐。”
“它被完全掌控着,可掌控者心甘情愿为这个还没有思想的存在奉献。自它出现以后,母亲吃的每一口饭、喝的每一口水,全都是为了它。彼此掌控,又彼此奉献,世间再也找不到另一件能将自私与无私如此完美地结合起来的事情。”
“但是卡佩夫人说,她很快乐。元帅,您知道吗,我曾经也像这样快乐过。”
钟情的瞳色因湿润变得更深,然而却看不出情绪,像涌动的暗流,将所有旁人的窥伺都吞噬进去。
安德烈意识到了什么,他无法说出任何话。
“罗素博士误诊后,有整整一周的时间,我都以为我已经怀孕。你一定很难理解有人会爱上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我以前也不相信,我总觉得爱是建立在很多东西之上的奢侈品。但有时候爱就是这样毫无理由,甚至不能察觉。我爱那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孩子,因为它与我血脉相连,还因为……它是严楫的遗腹子。”
“我是因为严楫而爱他。”
“有人告诉我,两年前,您将自己的军舰控制权交给次帅,然后坐着严楫的军舰,和他一起前往虫族巢穴。是真的吗?”
安德烈没有回答,反问道:“是谁告诉你的?是严楫?”声音喑哑得近乎狼狈。
“您答应我会和严楫一起回来,可回来的只有您一个人。宴会上严楫从始至终不曾提起孩子的事,或许他从来就没看到过罗素博士的讯息。那么,兰凯斯特元帅,您看见了吗?”
“是罗斯蒙德?”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钟情声音轻得像是刚出口就要消散在空气里,“您为什么这么恨严楫呢?”
安德烈唇角微动。
终于还是到了这一步。自严楫死而复生,他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每分每秒都是临行前的煎熬,直到今日铡刀落下。
他清晰地听见身体中有什么东西碎裂开来,面上却仍旧如同古井无波,连声音也毫无起伏。
“我不恨他。我只是渴望得到我想要的。”
但光屏上发来的那条讯息意味着他将永远只能妄想。
或许连严楫都不会比他更清楚那那颗胚胎的影响力。他曾见过严楫离开后在玫瑰园一坐就是一整天的钟情,不过是一朵有着严楫信息素气息的花,就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占据他全部时间,何况一个流着严楫血脉的孩子?
只要有严楫在,钟情便再也看不到其他人。就像有无形的丝线将他们紧密联系起来,任由旁观者费尽力气,也插不进去。
钟情将杯子里的酒一口饮尽,酒精让他的眼神略微迷离,他自嘲一笑。
“原来,最该怪的是我自己。怪我不该在十年前遇见您,更不该在两年前接受您的帮助。”
安德烈心中狠狠一缩。
“您说,我的一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生呢?既然是Omega,为什么要给我可以匹敌Alpha的身体素质?既然成为军人,为什么刚上战场就变成残废?”
钟情给自己重新倒了一杯酒,在安德烈想要开口阻止前笑着问道,“元帅要来一杯吗?”
他不等安德烈回答就仰头把杯子里的酒全部灌进嘴里。然后低头擦去嘴角的酒渍,顺便带走眼角因为酒精刺激渗出的一点眼泪。
“您说,我究竟是谁?”
“如果我是严楫的妻子,为什么不在听到死讯的那一刻就为他殉情?如果我是您的妻子,为什么不能忘记从前的事情,全心全意地爱您?”
“您告诉我,要靠着别人施舍和强迫才能活下去的我……这样的我到底是谁?”
从喉咙深处涌上来的血液把他呛了一下,猛烈的咳嗽间杂着自嘲的笑声。
钟情看着向他飞奔过来的、从来没有这样恐惧过的安德烈,醉意朦胧地向他举杯:
“元帅要来一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