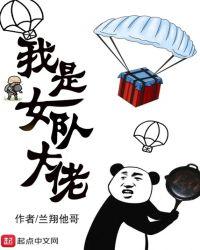精英小说>明月在窗 > 18第十八章 要除名(第3页)
18第十八章 要除名(第3页)
“怕什么?”
“怕梁映这人行事偏激,受不得委屈,若走之前闹上一笔,弄得人尽皆知。届时恐怕会让真太子发觉立德修身不过虚言,寒了心而致使教化不成,我与山长怕是同罪……”
“……”
庄严发现林清樾答得循规蹈矩,实则把诈她的话一一避过。本来只要她在梁映这件事上解释,无论偏向与否都会坐实他的论断。可她倒好,先引他猜疑外人,这会儿又搬出林氏来。
在族中,无论明部暗部,只要是接了指令的,命就不分贵贱。
饶他是明部花多年心血培养出的德高望重的大儒,不遵照指令,和林清樾一样会收到族中惩戒。
庄严指尖一下一下点着书案上梁映最新呈上来的自讨书,那里面的内容,他倒也看过。字迹虽难入眼,不过少年冤屈跃然纸上,真要错怪,确实有失偏颇。
“那若不能肯定,梁映就这么不管了?”
林清樾笑了笑,望向已经动摇的山长,朗声道。
“当然要管。既然梁映已被针对,何不干脆假戏真做,以他为靶,揪出书院之中心怀不轨之人?”
-
一夜过去。
梁映在被晨光刺透眼帘后,摸着睡得僵硬的脖颈坐起身。
“早啊,映兄,看样子你昨日睡得还不错。”
待梁映绕出屏风,穿戴齐整的林樾已然端正坐在桌前烹茶调香了。
梁映没有否认,此次虽是危机,也是守株待兔。
藏在暗处的人,不管如何今日总要动手。
他只需等着一醒来看看有何蛛丝马迹,寻着找过去就是了。
梁映心情不错地去了冷潭洗漱回来。
这会儿,林樾面前已经摆开脂粉,静静待他。
梁映也不再扭捏,一回生二回熟地坐了过去,下颚微抬便于他提笔描绘。
柔韧的笔尖在高挺的鼻梁扫过,林清樾画着画着,发觉梁映正一眨不眨盯着她手中的笔尖,大抵还没意识到自己黑沉的眸子快要对到一块去了,显得不太聪明。
“怎么了?”林清樾翘着唇角,边画边问。
梁映没有避讳,“怕没时间学,自当好好看看。”
林清樾手下蓦地顿了顿,“映兄,未免太灰心。”
“灰心”的梁映自顾自叹了一声。
“既然有心加害,若只是给我一个无关痛痒的惩戒未免太大题小做了。”
林清樾收笔,恨铁不成钢的怒气最终化为两指,飞速敲在梁映额角。
“映兄,读书机会不易,自当珍惜才是。”
梁映摸了摸额角,这林樾说话温柔,手劲倒是不小。
“哎,怎么走了?这簪子怎么束发?我还没学会呢。”
望着莫名走远的人,梁映掂了掂手里林樾送他的玉竹簪,笨手笨脚地抓起头发胡乱盘了个乱乱松松的髻,便跟着出了学舍。
-
在长衡书院,无论要去哪一斋上课的斋堂,四斋学子都要先穿过最外一进,也是最大的斋堂明心堂。明心堂平日里并不用于上课,多是用来讲演或是进行如释菜礼一般的全书院的典仪。
今日本该穿行过明心堂的学子都不由的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