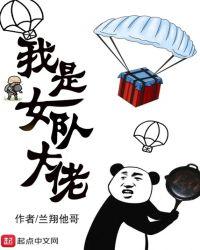精英小说>流水浮灯 > 第28章(第1页)
第28章(第1页)
不只是他,村中其他人也会为我伤心的罢。如果他们能够见到此刻的我,也一定会欢喜异常的罢。我的家乡是个极为淳朴的小山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家户户都鸡犬相闻。如果此刻我带着麟儿回到家乡,一定会有村民络绎地前来拜访,坐在温热的炕头通宵达旦地与我叙家常。这些曾经再熟悉不过的场景,以前从不曾在乎过,可如今想来,我竟是那样地渴望。
多余的思绪,我尽量不想让翩翩察觉。可是还是有些时候,它们会被我不经意地表达出来。
一日我问她:“难道这山中除了我们一家和花城一家之外,再无其他人居住吗?”
“或许还会有其他人罢,”她淡淡地说,“但从来就没有过来往,所以也和没有一样。”
“如果有其他人住,为什么不去拜访一下呢?”
“为什么要拜访呢?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的意思是……”我窘迫地解释道,“终年只有我和你对着,偶尔见见花城,但是还是太冷清了。如果有多些人来往,岂不是更好?”
“要那么多人来往做什么呢?”她奇怪地看着我,“我们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还要说什么,但看着她那张仿佛从未被尘世沧桑浸染过的脸,突然便失去了所有语言。与此同时,内心深处突然泛起淡淡的寂寞。
六
我发现我是寂寞的。
也许是因为我太不知足。可是在这样与世隔绝的云端,每日所见的只有密林深山和缓缓流动的白云,时间缓慢得如同凝固,一刻和一日并没有什么区别,一日和一年也无任何区别,换了别的尘世中人,又焉能不寂寞。
甚至是那初次吃时觉得有如琼露的蕉叶剪成的食物,久了我也开始觉得厌烦。溪水变成的佳酿固然清醇,但家乡辛辣的青稞酒,也未尝不令人怀念。
一日我问翩翩:“既然蕉叶能剪成食物,为什么你总是只剪饼、鸡、鱼这几样,为什么不剪些别的食物来吃呢?”
她奇怪地看着我,问:“你还想吃什么呢?”
我说:“世间可吃的东西多了去了。我年少时在金陵,吃过他们从深海中捞上来的鲛翅,用鸡汤细细煨上三日,入口即化,再无其他东西比得上它的香滑。下雪的时候,会有快马从千里之外送来熊掌,凤凰楼的厨子最善于用鲍汁来炖,炖的时候那香味能一直从金陵飞到钱塘。你既然可以随意用蕉叶剪出食物,为什么不剪一些山珍海味来品尝,而要终日吃着这些毫无新意的鸡鱼饼呢?”
“你是觉得鸡鱼饼吃不饱吗?”她问我,而我摇摇头。
“那如果让你终日只吃熊掌,你会比现在更快乐吗?”她又问。
她的话,自然是有她的道理的。我深深明白,以致再无别的话可说。可是纵然无话可说,心底的寂寞,却依然难以消除。
心中的寂寞,我只有自顾自地讲给我未经世事的儿子听。他起初只是懵懂地听,但听得久了,也似有些明白了。
他开始追问。当我说起山下日夜奔流的河川时,他便好奇地问我那些河流最终流向何方;当我描述着那些雄伟壮丽的宫阙是如何高耸入云时,他便问修建那些宫阙的人去了哪里。我的孩子,虽然自出生起便一直生活在这云端,不曾见过别的什么人,但是他骨子里流淌着的我的血,却让他渐渐生出如我一样对尘世的向往来。
他一日一日地大了,也一日一日地忧郁起来。没事的时候时常坐在山边的乱石上,默默看着脚下的云。一日翩翩问他在看什么,他却反问道:
“云的下面,是什么?”
“云的下面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那与我们无关。”翩翩告诉他。
“可是,阿爹告诉我,他便是从云下来的。他说云下有另一个世界,一个很热闹很好玩的世界。那里有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少年,我可以与他们一起游玩一起读书。那里还有我的爷爷,他若见到我,一定很开心。”
翩翩默然半晌,却将我拉到一边,异常温和地说:
“你是不是想要回去了?”
我看着她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以前年少不更事,只顾远游,从未尽过一天孝道。如今我也做了父亲,渐渐明白了父亲的苦。我想带你们下山,为父亲养老送终。”
她没有不悦,仍是温和地说:“你想要回去尽孝,也是应该的。让阿爹看看他的亲孙子,也是好的。可是我却不能与你同去。”
“为什么呢?”我问道。